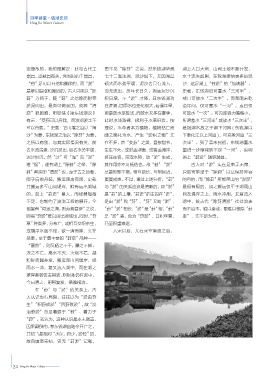Page 26 - 宁波水文化17期
P. 26
季讲堂·钱湖史话
Ning Bo Water Culture
定缘故的。我的理解是:此与古代工 更不见“除葑”之说。然东钱湖毕竟 湖上人口大增,山间土地不断开发,
水土流失加剧,东钱湖接纳更多的泥
器具、运载具有关。凭当时的工器具, 七十二溪注湖,泥沙俱下,又因湖盆 沙,这是湖上“葑淤”的“加速器”。
史载,东钱湖旧可蓄水“三河半”,
“葑”是可以开挖和搬移的,而“淤” 硕大而水势平缓,泥沙者只有流入, 或曰可放水“三次半”,而至南宋乾
道年间,仅可蓄水“一河”,或曰仅
是难以提取和搬运的,古人只能以“除 而无流出,历年长日久,湖底泥沙沉 可放水“一次”,可见库容大幅缩小。
所谓蓄水“三河半”或放水“三次半”,
葑”为抓手,随“葑”之挖除而附带 积日增,不“淤”才怪。且东钱湖功 是指湖水放之于湖下河网 ( 东钱湖以
下奉化江以上河道 ),可充盈河道“三
淤泥同出,是尚可做到的,纯粹“清 在灌溉,四季水位变化很大,若遇年旱, 次半”。到了清末民初,东钱湖蓄水
量进一步缩减到不足“一河”,说明
淤”很困难。明邱绪《浚东钱湖议》 更是放水至极浅,而放水又多在夏季, 湖上“葑淤”越积越甚。
有云 :“茭葑可以舟载,而浚湖淤土不 此时水浅滩裸,极利于水草旺发。按 古人对“淤”实在是束手无策,
只能寄希望于“除葑”以达保持库容
可以舟载。”史载:它山堰之治以“淘 理说,水草者本为植物,植物枯亡而 的目的,而“除葑”所能带出的“淤泥”
是很有限的,加之搬运仅至于湖周山
沙”为要,东钱湖之治以“除葑”为要。 随之腐化为水,产生“淤积之物”实 间及堤岸之上,雨水冲刷,又复流入
湖中,故古代“除葑清淤”往往治表
之所以有别,与其实际情况有关,前 在不多,然“茭葑”之类,盘根错节, 而不治本,难以奏效,更难以根除“葑
患”,实不足为奇。
者水流湍激,沙沉泥出,后者水势平缓, 生生不死,或封盖湖面,或覆盖滩岸,
泥沙俱沉,然“沙”可“淘”而“淤” 挤压库容,滞涩水势,助“淤”生成,
难“捉”,遂有湖上“除葑”之举,“除 其作用亦不可低估也。故“葑”“淤”
葑”者实即“清淤”也。至于古之运载, 总是形影不离,相互助长,互相促进,
限于肩挑舟装,搬运距离有限,史载 屡屡成患。不过,通过上述分析,“葑”
其搬运多至山间堤岸,鲜有运出湖域 与“淤”的关系应该是清晰的,即“淤”
的。加上“葑淤”量大,而经费每每 是“葑”的土壤,“葑淤”的主因在“淤”,
不足,也制约了浚治工程的展开。全 是由“淤”致“葑”,“葑”又助“淤”,
祖望有“欲运之海,则劳费甚侈”之说, “葑”“淤”相长,“淤”是“葑”根,“葑”
即指“葑淤”难以运出湖域也。同时,“葑 是“淤”表,合为“葑淤”,日积年累,
草”种类多,分布广,或相互交织杂生, 乃至积重难返。
或飘浮水面不定,欲一清而除,实非 入宋以后,尤在宋室南渡之后,
易事。至于最主要的“葑草”品种——
“蔓荊”,则又晒之不干,曝之不毙,
冻之不亡,离水不灭,火烧不着,越
粉碎而越多发,搬运至山间堤岸,经
雨水一冲,复又流入湖中,而在湖之
滩岸者若仅去其表,则根茎仍在泥中,
今日清之,明朝复发,确难根治。
在“葑”与“淤”的关系上,古
人认识也有局限,往往以为“淤由葑
生”“积葑成淤”“因葑致淤”,故“浚
治葑淤”总是着眼于“葑”、着力于
“葑”。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本末倒置、
因果颠倒的。考东钱湖自陆令开广之,
其初当是相对“水深、葑少、淤轻”的,
故自唐至宋初,史无“葑淤”记载,
24 Ning Bo Water Culture
Ning Bo Water Culture
定缘故的。我的理解是:此与古代工 更不见“除葑”之说。然东钱湖毕竟 湖上人口大增,山间土地不断开发,
水土流失加剧,东钱湖接纳更多的泥
器具、运载具有关。凭当时的工器具, 七十二溪注湖,泥沙俱下,又因湖盆 沙,这是湖上“葑淤”的“加速器”。
史载,东钱湖旧可蓄水“三河半”,
“葑”是可以开挖和搬移的,而“淤” 硕大而水势平缓,泥沙者只有流入, 或曰可放水“三次半”,而至南宋乾
道年间,仅可蓄水“一河”,或曰仅
是难以提取和搬运的,古人只能以“除 而无流出,历年长日久,湖底泥沙沉 可放水“一次”,可见库容大幅缩小。
所谓蓄水“三河半”或放水“三次半”,
葑”为抓手,随“葑”之挖除而附带 积日增,不“淤”才怪。且东钱湖功 是指湖水放之于湖下河网 ( 东钱湖以
下奉化江以上河道 ),可充盈河道“三
淤泥同出,是尚可做到的,纯粹“清 在灌溉,四季水位变化很大,若遇年旱, 次半”。到了清末民初,东钱湖蓄水
量进一步缩减到不足“一河”,说明
淤”很困难。明邱绪《浚东钱湖议》 更是放水至极浅,而放水又多在夏季, 湖上“葑淤”越积越甚。
有云 :“茭葑可以舟载,而浚湖淤土不 此时水浅滩裸,极利于水草旺发。按 古人对“淤”实在是束手无策,
只能寄希望于“除葑”以达保持库容
可以舟载。”史载:它山堰之治以“淘 理说,水草者本为植物,植物枯亡而 的目的,而“除葑”所能带出的“淤泥”
是很有限的,加之搬运仅至于湖周山
沙”为要,东钱湖之治以“除葑”为要。 随之腐化为水,产生“淤积之物”实 间及堤岸之上,雨水冲刷,又复流入
湖中,故古代“除葑清淤”往往治表
之所以有别,与其实际情况有关,前 在不多,然“茭葑”之类,盘根错节, 而不治本,难以奏效,更难以根除“葑
患”,实不足为奇。
者水流湍激,沙沉泥出,后者水势平缓, 生生不死,或封盖湖面,或覆盖滩岸,
泥沙俱沉,然“沙”可“淘”而“淤” 挤压库容,滞涩水势,助“淤”生成,
难“捉”,遂有湖上“除葑”之举,“除 其作用亦不可低估也。故“葑”“淤”
葑”者实即“清淤”也。至于古之运载, 总是形影不离,相互助长,互相促进,
限于肩挑舟装,搬运距离有限,史载 屡屡成患。不过,通过上述分析,“葑”
其搬运多至山间堤岸,鲜有运出湖域 与“淤”的关系应该是清晰的,即“淤”
的。加上“葑淤”量大,而经费每每 是“葑”的土壤,“葑淤”的主因在“淤”,
不足,也制约了浚治工程的展开。全 是由“淤”致“葑”,“葑”又助“淤”,
祖望有“欲运之海,则劳费甚侈”之说, “葑”“淤”相长,“淤”是“葑”根,“葑”
即指“葑淤”难以运出湖域也。同时,“葑 是“淤”表,合为“葑淤”,日积年累,
草”种类多,分布广,或相互交织杂生, 乃至积重难返。
或飘浮水面不定,欲一清而除,实非 入宋以后,尤在宋室南渡之后,
易事。至于最主要的“葑草”品种——
“蔓荊”,则又晒之不干,曝之不毙,
冻之不亡,离水不灭,火烧不着,越
粉碎而越多发,搬运至山间堤岸,经
雨水一冲,复又流入湖中,而在湖之
滩岸者若仅去其表,则根茎仍在泥中,
今日清之,明朝复发,确难根治。
在“葑”与“淤”的关系上,古
人认识也有局限,往往以为“淤由葑
生”“积葑成淤”“因葑致淤”,故“浚
治葑淤”总是着眼于“葑”、着力于
“葑”。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本末倒置、
因果颠倒的。考东钱湖自陆令开广之,
其初当是相对“水深、葑少、淤轻”的,
故自唐至宋初,史无“葑淤”记载,
24 Ning Bo Water Culture